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méi)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méi)有后顧之憂
來(lái)源:期刊VIP網(wǎng)所屬分類:綜合論文時(shí)間:瀏覽:次
提 要:烏爾第三王朝貢物中心作為中央直屬的行政管理機(jī)構(gòu),其檔案管理和保存能力幾乎代表了當(dāng)時(shí)所能達(dá)到的最高水準(zhǔn)。本文通過(guò)對(duì)貢物中心出土的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梳理分析,并結(jié)合前人對(duì)貢物中心機(jī)構(gòu)研究的大量成果,認(rèn)為貢物中心很可能存在一個(gè)專門的檔案部門,這個(gè)檔案部門隨著檔案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演化出相對(duì)成熟的檔案管理制度。這不僅對(duì)研究烏爾第三王朝整體檔案管理制度提供了幫助,也為深化對(duì)這一時(shí)期的政治經(jīng)濟(jì)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
關(guān)鍵詞:烏爾第三王朝;貢物中心;檔案管理;蘇美爾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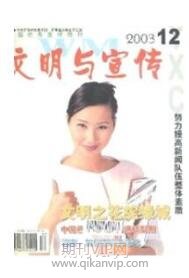
《文明與宣傳》堅(jiān)持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的方向,堅(jiān)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dǎo),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理論與實(shí)際相結(jié)合的嚴(yán)謹(jǐn)學(xué)風(fēng),傳播先進(jìn)的科學(xué)文化知識(shí),弘揚(yáng)民族科學(xué)文化,促進(jìn)國(guó)際科學(xué)文化交流,探索防災(zāi)科技教育、教學(xué)及管理諸方面的規(guī)律,活躍教學(xué)與科研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為教學(xué)與科研服務(wù)
烏爾第三王朝(約公元前2112—2004年)是首個(gè)由蘇美爾人建立的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制國(guó)家,歷經(jīng)烏爾那姆(Ur-Nammu)、舒勒吉(?ulgi)、阿馬爾辛(Amar-Sin)、舒辛(?u-Sin)、伊比辛(Ibbi-Sin)五王,在第二任王統(tǒng)治時(shí)期臻于鼎盛。根據(jù)亞述學(xué)研究網(wǎng)站BDTNS及CDLI收錄統(tǒng)計(jì),1目前烏爾第三王朝出土的檔案類泥板超過(guò)9萬(wàn)塊,如此大量的檔案文獻(xiàn)能夠保存至今,既得益于當(dāng)?shù)匾椎靡妆4娴臅鴮懖牧希搽x不開(kāi)當(dāng)時(shí)的檔案保存意識(shí)與管理方法。2舒勒吉在其統(tǒng)治時(shí)期建立了王室貢物調(diào)撥中心(é-Puziri?-Daga,以下簡(jiǎn)稱“貢物中心”),負(fù)責(zé)接管全國(guó)進(jìn)貢的各類物資并進(jìn)行再分配,自此大量記錄貢物調(diào)撥的檔案文獻(xiàn)開(kāi)始涌現(xiàn),直至伊比辛二年貢物中心關(guān)閉。作為直屬于國(guó)王的行政管理機(jī)構(gòu),貢物中心的檔案管理是由中央政府主導(dǎo)的官方行為,相較于地方檔案的管理更為規(guī)范與完善。由于盜挖猖獗,考古現(xiàn)場(chǎng)多被破壞,加之缺乏直接的文獻(xiàn)記載,所以烏爾第三王朝貢物中心的檔案管理的研究面臨很大困難。有鑒于此,本文擬從貢物中心出土的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及可能存在的檔案管理官員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入手,結(jié)合貢物中心整體管理運(yùn)行模式的研究,為該問(wèn)題的推進(jìn)做出些許貢獻(xiàn)。
一、貢物中心檔案管理的相關(guān)研究
亞述學(xué)界對(duì)貢物中心的研究始于20世紀(jì)初,早在1910年便有貢物中心檔案文獻(xiàn)被集成出版,1此后貢物中心的泥板文書陸續(xù)在世界各地發(fā)表,經(jīng)過(guò)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洗禮,國(guó)際亞述學(xué)逐步走向科學(xué)研究的道路,穩(wěn)定的國(guó)際局勢(shì)使得文獻(xiàn)資料的互通成為可能。1961年,瓊斯(Tom B. Jones)與斯奈德(John W. Snyder)攜手出版了對(duì)烏爾第三王朝貢物中心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烏爾第三王朝蘇美爾經(jīng)濟(jì)文獻(xiàn)》(Sumerian Economic Texts from the Third Ur Dynasty),書中不僅梳理了貢物中心的核心組織機(jī)構(gòu),還有對(duì)作為“國(guó)使和看門人”(sukkal ì-du8)的那冉伊里(即下文要論述的檔案官員之一)的分析,奠定了之后烏爾第三王朝經(jīng)濟(jì)研究,特別是貢物中心研究的框架。2而后,雖有學(xué)者在各種著作中零散提及貢物中心,但直到1989年日本學(xué)者前田徹(Tohru Maeda)的文章發(fā)表,學(xué)界對(duì)貢物中心機(jī)構(gòu)的認(rèn)識(shí)才向前推進(jìn)了一大步。
3文中通過(guò)整理分析貢入類(mu-tum2)文獻(xiàn),不僅梳理出不少貢物中心的內(nèi)部機(jī)構(gòu),還根據(jù)文獻(xiàn)中“土地”(a-?a3)一詞推測(cè)貢物中心附近有眾多包含附屬機(jī)構(gòu)的衛(wèi)星城鎮(zhèn),而在諸如烏爾(Ur)、烏魯克(Uruk)等主要城市中可能也存在附屬或分支機(jī)構(gòu)。4雖然他的文章僅分析了一類檔案文獻(xiàn),難以對(duì)貢物中心的整體進(jìn)行更加有效的研究,但其對(duì)貢物中心附屬機(jī)構(gòu)的推測(cè)引起了學(xué)界對(duì)貢物中心管理運(yùn)行和機(jī)構(gòu)性質(zhì)的不同思考,筆者將在后文討論貢物中心機(jī)構(gòu)性質(zhì)時(shí)詳述。
3年后,西格瑞斯特(Marcel Sigrist)在其學(xué)術(shù)專著《德萊海姆》(Drehem,貢物中心遺址在今伊拉克的地區(qū)名稱)中,通過(guò)對(duì)已發(fā)表大部分檔案文獻(xiàn)和研究的整體梳理,確定了貢物中心及其附屬機(jī)構(gòu)的基本組織框架。他主要依托檔案文獻(xiàn)分析存在的部門,卻忽視了最顯而易見(jiàn)的部分,即如此大量完整的檔案文獻(xiàn)在盜挖的情況下問(wèn)世,很可能表明在貢物中心存在著一個(gè)專門負(fù)責(zé)檔案管理的機(jī)構(gòu)。遺憾的是,西格瑞斯特雖在書中注意到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封泥和標(biāo)簽的作用,卻未能展開(kāi)討論。而且,他對(duì)那冉伊里的地位作用的認(rèn)識(shí)并沒(méi)有突破1961年以來(lái)的研究。5前田徹在1994年對(duì)貢物中心總督主祭期(bala-ensi2)文獻(xiàn)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檔案管理官員及機(jī)構(gòu)的術(shù)語(yǔ)。通過(guò)對(duì)相同類型檔案文獻(xiàn)的分析得出那冉伊里、巴巴提、沙臘坎和盧旮勒伊提達(dá)是同一機(jī)構(gòu)的官員,其中那冉伊里與巴巴提是主管官員并且是前后任,而沙臘坎和盧旮勒伊提達(dá)是兩人的下屬,甚至還推測(cè)盧旮勒伊提達(dá)的繼任者為那維爾伊里,并根據(jù)巴巴提的印章中含有檔案員的頭銜推測(cè)那冉伊里也應(yīng)承擔(dān)了相應(yīng)的職責(zé)。6然而,前田徹的研究仍舊是建立在對(duì)單一類型文獻(xiàn)即總督主祭期檔案的分析上,雖然他提出了
檔案管理官員及機(jī)構(gòu)的概念,但是并未明確其所使用的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的作用,也未對(duì)管理流程等方面進(jìn)行細(xì)節(jié)研究。
需要說(shuō)明的是,在早期翻譯原始泥板的過(guò)程中,學(xué)者已經(jīng)注意到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的存在。1914年,凱澤(Clarence E. Keiser)將公元前3千紀(jì)的此類文獻(xiàn)分為4類:繩結(jié)封泥、泥板標(biāo)簽、檔案箱標(biāo)簽和動(dòng)物標(biāo)簽,奠定了該類文獻(xiàn)的基礎(chǔ)分類標(biāo)準(zhǔn)。1圖索帕羅盧(Christina Tsouparopoulou)于2008年在其博士論文中整理了貢物中心的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大致梳理出檔案的復(fù)寫、傳遞、密封、保存等環(huán)節(jié),但其中心論點(diǎn)在于論證貢物中心本身即為檔案管理機(jī)構(gòu),對(duì)相關(guān)文獻(xiàn)的分析側(cè)重器型與內(nèi)容、功能、部門的聯(lián)系,忽視了對(duì)文獻(xiàn)內(nèi)容本身的挖掘,對(duì)檔案管理官員的分析更是一筆帶過(guò)。
22017年,圖索帕羅盧又撰文詳細(xì)論述了貢物中心的檔案管理,將流程明確為臨時(shí)存放、密封與拆封保存三步,推測(cè)每一步的時(shí)間周期,并補(bǔ)充了檔案袋(箱)的容量及燒過(guò)的封泥隨檔案一起保存等細(xì)節(jié)。3其表述看似論據(jù)充分,但存在以下問(wèn)題:
1、對(duì)兩種主要文獻(xiàn)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含混不清,導(dǎo)致一些原始文獻(xiàn)的錯(cuò)分與遺漏。因此本文在討論時(shí),以中空球體或多面體的外形及印章作為繩結(jié)封泥的劃定標(biāo)準(zhǔn),避免了與檔案箱標(biāo)簽產(chǎn)生混淆;
2、把主要精力放在討論繩結(jié)封泥的器型上,一些結(jié)論含有很大的主觀臆測(cè)與牽強(qiáng)附會(huì)成分,如對(duì)封泥形狀與功能關(guān)聯(lián)性的解釋、由術(shù)語(yǔ)“?-tum”推斷檔案分類流程等過(guò)于草率,與之不符的原始文獻(xiàn)俯拾皆是;
3、忽視了前田徹所定義的檔案管理官員及機(jī)構(gòu)的內(nèi)容,并未全面分析檔案管理類文獻(xiàn)呈現(xiàn)的管理內(nèi)容。由此可見(jiàn),學(xué)界對(duì)貢物中心檔案管理方式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自2002年起,吳宇虹教授主持的《烏爾第三王朝貢物調(diào)撥中心檔案重建項(xiàng)目》(Archives of Animal Center of Ur-III Dynasty in Drehem Project)開(kāi)始對(duì)貢物中心的檔案文獻(xiàn)進(jìn)行整理翻譯,時(shí)至今日已基本完成對(duì)貢物中心重要官員的檔案重建,并完成了50余篇中外期刊論文和碩博學(xué)位論文的寫作,正是有了這樣的研究基礎(chǔ),本文才得以從更宏觀的視角把握貢物中心檔案管理方式流程及組織架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