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摘 要:在農村產業化的推進過程中,市場化一直是國家強力推行的手段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以打破傳統小農的“生存經濟”,使之實現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但實踐中卻導致農村發展更加依附于市場資本與政策制度。基于此視角,對黔東南T縣縣域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分析表明,經過多年的產業化實踐,農村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傳統小手工業通過產業化與市場經濟產生勾連,使農村地區全面卷入市場經濟,對市場經濟產生深刻的寄生性,同時在寄生中獲得有限的發展,從而拉大了城鄉間的發展差距。農村產業化發展中經濟效應的發揮,需要和自我發展能力緊密結合起來,破除“寄生性發展”的困局,真正實現農村的內生性發展。
關鍵詞:黔東南;產業扶貧;項目扶貧;農村產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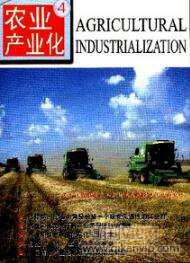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產業化是中國農村發展政策及鄉村振興的核心要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小農經濟一直被視為改造的對象,以此不斷推動農村產業發展。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央連續出臺了有關農村發展與產業化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從改革初期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到當下的各種產業發展模式,農村產業被寄予了培植農村內生發展動力的期待,圍繞頂層設計、資源配套到基層實踐,尤其是在精準扶貧重要思想的實踐中,農村產業發展一直是眾多扶貧措施包括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移民、社會兜底等的重中之重,產業化被置于“五個一批”的龍頭地位,傾注了國家和社會各行業的極大資源。客觀來說,農村產業化在帶動農村人口脫貧致富上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同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根據當下的實踐來看,其發展仍然因為資源浪費、分配不公、效果不夠理想而備受質疑。在中央財政扶貧資金自上而下輸入的過程中,因為“時間緊、任務重”導致貧困治理所需要的時間和空間受到極大壓縮,使地方政府實施產業扶貧面臨“短平快”的境況,向上負責的利益導向成為產業扶貧項目在落地實施的過程中目標偏離的制度導因[1]。在這一背景下,以產業扶貧的實施為主導的資源輸入又因為村莊治理的弱化使扶貧資源遭遇精英俘獲[2],形成相應的分利秩序[3],并使扶貧項目的發展結果為大戶和私人企業占有,貧困人口往往處于產業發展的邊緣地位[4]。而且市場經濟的強勢地位、農業的高風險特性以及農村人口的脆弱性貧困更使農村產業的推進與發展進退維谷。
在這樣的現實困境中,提高農村產業化發展的市場面向和經濟效益幾乎是所有產業扶貧項目追求的目標。在產業鏈的供給與價值鏈的整合等方面,產業扶貧雖然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效果并不令人滿意。由此,我們需要發問的是,在精準扶貧作為一項政治任務的背景下,外部資源的大量輸入和內生發展力量二者共同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化”會給農村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讓農村社會走向什么樣的發展境地呢?與這一問題緊密相關的是農民的生存境況和小農經濟的發展遭遇。因此,產業扶貧項目的實施應當放于農村社會的整體發展框架和城鄉關系中來進行綜合考察。本文以黔東南T縣的縣域農業產業化發展為研究對象,以地方政府推動的休閑園區建設、東西協作中的產業幫扶代表外援力量,以本地苗族刺繡業的發展作為內生發展力量,粗略地探索和分析內外兩種力量是如何共同形塑了如今T縣農村社會的發展狀況。
二、文獻回顧與分析視角
(一)文獻回顧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小農經濟一直被視為改造的對象,以對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可以說建成現代性的“產業化”農業即是傳統農業改造的目標。當前,農村產業發展已成為振興鄉村的重要推手,這其中小農經濟面臨什么樣的遭遇,農村產業化發展的背后有著怎樣的困局,尤其是產業扶貧項目為何難以“落地開花”,既有的相關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和視角。
1.小農“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的歷史進程中,“農民學”經典關注的焦點是市場資本和商品力量不斷加大對鄉村的滲透,小農作為傳統農業社會主體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生存是其行為準則的中心,該如何順應和完成這一轉變?中國當下也正經歷著這一轉變,在此轉變過程中,農民問題解決得成功與否,將直接關系到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目標的實現。斯科特通過對東南亞農業社會的研究,認為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包含著一個獨特的因素,即“生存理性”與“安全第一”的生存倫理,這一倫理根植于農村社會的經濟實踐之中。因為農業家庭不僅是生產單位,更是消費單位,處于首要地位的是滿足消費的功能以實現生存的目的。因此小農基于高風險性和高脆弱性的小農生產,會在生產行動選擇的過程優先考慮“安全第一”的生產安排,以能夠保障最低生活要求[5]。也由此形成了小農特有的生產性質,即生產水平低、自給自足、低度消費和分散性經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特性往往被認為是保守落后的、需要加以“改造”的。農村產業扶貧項目即是通過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同時建立風險化解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從而提高農村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對接能力,進而實現市場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但是這種改造卻又往往容易使農村、農業卷入另一種風險之中,即產生了小農如何對接大市場的困局。
2.“小農如何對接大市場”的發展困境
與農民生存倫理的處境相伴,國家對“小農改造”重視也直接促進了農村產業化的發展,重點以產業扶貧的方式擺脫“小農”自身的局限,使之逐漸成為市場經營的獨立主體。在實踐的過程中,諸多研究指出,農業產業因其地域的分散性和抵御自然風險的脆弱性,在面對市場的競爭中農民處于弱勢地位,加上農民對市場信息獲取的能力有限,共同構成他們在市場化處境中不得不面臨的現實困境[6]。但是,幫助小農戶對接大市場的產業扶貧政策,并不能達到令人滿意的預期效果,乃至遭遇失敗并產生了“小農境地”,國家面臨“改造農民”和“駕馭市場”的雙重困境。最后的結果不僅是小農自身的經濟利益受損,國家的農產品供給和價格穩定、糧食安全等全局性問題也受到影響[7]。因此,小農與國家都面臨著相應的困境。黃宗智認為小農戶、大市場同商業資本的交易是不平等的交易,具體分析了交易中“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其實主要不是科斯所看到的獲取信息,達成、擬訂和執行契約的成本,而是因為不對等權力關系而受人擺布所導致的高成本” [8]。所謂的龍頭企業,大多數并不是介入生產過程,而是與農戶簽訂單,其后負責收購、加工和銷售。即使是介入生產過程的企業,其生產的優勢依然是低廉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不能真正帶動農戶走進市場。而且“以龍頭企業為主導的農業產業化不僅不能充分帶動農戶的發展,而且會在市場交換中進一步掠奪農戶的勞動剩余,將農民置于發展的附屬地位,從而成就企業的資本積累”[9]。如此看來,小農能不能與大市場對接,關鍵在于市場與資本能否平等交易。如果小農不能真正對接大市場,所謂系列農業治理政策也就走了不多遠,所謂的大市場也成不了氣候,最終受損的還是小農。
推薦閱讀:《農業工程技術.農業產業化》國家級農業論文投稿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