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一、媒介考古學需要“中國化”“在地化”
問:正如您之前在《傳播研究的媒介學轉向》一文中所引述的,媒介學是一門“來自遠方”的學科,那么在中國的本土語境中,媒介考古研究會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作為研究人員,我們應該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潘祥輝:我認為媒介考古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是如何把媒介考古學“中國化”“在地化”。從名稱上來說,媒介考古學固然是西方學者首先提出來的,但我認為誰也沒有權力壟斷它,作為一種研究取向,它完全可以在地化。在中國本土語境中找到自己獨特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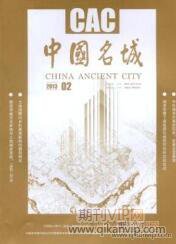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拿來主義”,包括引進的大部分理論,實際上還是在西方的框架上生搬硬套。所以無論是我們現在研究的媒介考古學,還是華夏傳播學,我們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研究問題,在此基礎上,推進我們研究的本土化,這個最重要。記得李金銓教授講過:西方社會已經定型了幾百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太大的變化。而我們中國社會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轉型,我們的問題、學術關懷和他們的完全不一樣。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學術模式去做,越做越細,雖然很精致,但這是一種“精致的平庸”,會造成學術研究的“內卷化”。
那么,我們研究人員應該怎么尋找問題?我認為還是要多觀察、多思考、多體認。“體認”是很重要的,其實很多的媒介和傳播現象,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實踐中,需要我們去發現和開掘。當然,也包括多閱讀,閱讀是間接經驗的積累,是和前人的對話,非常重要。做華夏傳播研究不一定說就是閱讀中國的東西,也要有對西方經典和理論的閱讀,只有把別人的東西消化了之后,融會貫通,我們才能夠打開視野,找到我們自己的研究問題。否則問題都找不到,“有特色”的研究就更無從談起。
二、中國古代也有很多“新媒體”
問:您對華夏傳播學、中國媒介社會學、政治傳播學等領域都有所涉獵和專門研究,近年來您主要投入“媒介考古學”的研究方向,這種轉變原因是什么?影響您的關鍵性因素是什么?
潘祥輝:投入媒介考古學的研究主要還是和我自己的學科背景有關。我個人原來是中文系出身,研究生讀的是古代漢語,博士后讀的是歷史學。我自己的學科背景是比較獨特的,在研究媒介考古這一領域有一定的優勢。
對于歷史上的東西,我們新聞傳播學界有興趣的或是能夠去做這方面研究的人比較少。現今主流學術觀點認為,新聞傳播學追求的是“新”,一直在追“新媒體”,但實際上中國古代也有很多“新媒體”,我們今天講的新媒體是在舊媒體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而舊媒體在歷史上也曾是新媒體。所以其實無所謂“新”和“舊”,“新”和“舊”只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概念。這種“以舊為新”的觀點就包含在“媒介考古學”的思想中。
我是從學術創新、學術興趣和學科背景等方面綜合考慮,才轉到研究媒介史、華夏傳播學、媒介考古學等方面來的。我希望對中國古代的一些傳播媒介,包括傳播思想、傳播觀念、傳播制度等做一個深入考察。為了區別于西方意義上的“媒介考古學”,我把這樣一種本土取向的研究稱為“傳播考古學”,當然,也可以稱之為“中國媒介考古學”研究。從研究的范圍上而言,媒介考古學主要側重在器物層面,也即我們現在談得很多的“媒介物質性”、有形的物質性媒介,而“傳播”的范圍要廣一些,除了器物媒介,也可以研究行為、儀式、聲音、思想等。所以我說的傳播考古學,與媒介考古學可以說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有跨學科的背景,也對跨學科研究非常感興趣,轉到這個領域,就是覺得這個領域值得研究,我也能在這個領域發揮自己的優勢。
實際上,做學術研究一定要找“薄弱”的環節,也就是所謂的“空白點”,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去做學術創新。研究新媒體可能“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但是研究古代媒介的那些東西,如果別人做不了,我覺得需要我去做,而且做這些事情是很有價值的,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我就會覺得有成就感。與此同時,我越研究越發現,這些“老古董”里面可挖掘的東西特別多,光憑我一個人的力量還不夠,還需要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三、中國媒介考古學研究方法需要和傳統考據學對接
問:您認為“媒介考古”方法在如今有何新意,和之前的主流研究方法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潘祥輝:這個問題要分“中國”和“西方”來看。西方的媒介考古學,像埃爾基·胡塔莫、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他們做的媒介考古學,實際上是借鑒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不過是把“知識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引入到了媒介學領域來,但是它的方法主要還是一種哲學思辨。
而我講的“媒介考古學”或者“傳播考古學”,更多的是結合了考古學、文字學、考據學的方法,這些方法最大的特色是與中國傳統的學問相對接。例如,怎么來考察中國古代的器物,怎么來研究中國的甲骨、青銅、文字,古代叫金石學或考據學,這個學問有它的一系列方法,具有很強的實證性。比如,考據學十分講究邏輯推理和例證完整,“無一字無來歷”,可以說是中國本土的一種實證研究方法。所以,我們的“媒介考古”研究方法和西方不同,它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事實上,“實證”這個詞,就是從傳統考據學中發展出來的。在傳統考據學的基礎上來做中國的媒介考古,是一種返本開新,這個是傳統學問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我們應該把它們發揚光大。同時,它也可以和西方的一些哲學思辨的研究或者和一些實證研究形成一種“對話”,用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四、中國文明越往前推和西方文明的差異就越大
問:既然提到了不同文明比較下的中國媒介考古學,您認為,不同文明中的“媒介考古”是否有普遍性?它們各自的特殊性又體現在哪里?
潘祥輝:文明的普遍性肯定是存在的,東西方文明有很多東西是相同的,這體現了人類文明的共通性。但顯然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我們把中國文明越往前推,它和西方文明的差異就越大。如果把秦漢時期的社會與羅馬社會去比較的話,差別就會特別大。比方說,西方人認為黃金很重要,王冠的材質也會選擇黃金作為一種權力的象征。但是在漢代以前的中國,黃金的使用很少,取而代之的是以“玉器”“鼎”(青銅器)等媒介作為權力的象征。比如,玉璽、青銅器都是權力媒介,它們的材質不是黃金。我們中國人講“一言九鼎”“問鼎中原”,就體現了青銅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你會發現,不同的文明下的媒介是各有其特殊性的。我們做媒介考古的研究,就是要挖掘出中國文明的獨特性,然后和西方的學者去進行“對話”。比方說,加拿大學者英尼斯寫過《帝國與傳播》,他講到了中國的紙、埃及的莎草紙,講這些或偏向時間或偏向空間的媒介對帝國的治理、帝國的擴張有什么樣的作用。但是他并沒有提到像中國的青銅器、玉器、甲骨等媒介載體。可能他不了解、也不知道這樣一些媒介。其實我們的青銅器上也是可以刻字的,這種鑄字方法甚至是活字印刷的一個源頭,西方人不了解中國文化,我們也能理解,那么我們中國人自己就要來研究。西方的青銅器和玉器都不發達,它們幾乎是沒有玉器文明的(除了美洲瑪雅文明),所以我們就要去研究中國特色的媒介歷史。像我自己做過的關于青銅器的研究,我就提出了“傳播史上的青銅時代”這一命題,它實際上就是一種和英尼斯“對話”的方式。中國傳播史上有過一個“青銅時代”,在這之前還有一個“玉器時代”,這是西方傳播史上所沒有的。而這些媒介在我們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推薦閱讀:創建文明城市論文怎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