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有后顧之憂
來源:期刊VIP網(wǎng)所屬分類:綜合論文時間:瀏覽:次
摘要:突發(fā)公共事件暴發(fā)時,公共管理者設(shè)立研發(fā)項目,研發(fā)機構(gòu)爭取立項資助。本文建立了一個動態(tài)不對稱信息模型,刻畫了研發(fā)機構(gòu)釋放能力類型信號、公共管理者甄別信號并進行研發(fā)補貼的過程。結(jié)論表明:突發(fā)公共事件暴發(fā)時,由于研發(fā)機構(gòu)對于事件起因的認識并不充足,所開展的研發(fā)活動往往是一種半自由式的發(fā)散性實驗探索。研發(fā)機構(gòu)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難度較小,成本也容易控制,各類研發(fā)機構(gòu)都傾向于釋放自己是高能力研發(fā)機構(gòu)的信號。由于公共管理者缺乏足夠時間和明確標準來判斷申報成果的研發(fā)質(zhì)量,難以準確甄別出研發(fā)機構(gòu)的真實能力類型。因此,公共管理者的最優(yōu)決策是給予所有申報者相對較高的研發(fā)補貼,但研發(fā)補貼的總額度有限。本文提出:要改善現(xiàn)有的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機制,公共管理者在日常的科技創(chuàng)新管理中應(yīng)采取深度參與的方式,完善突發(fā)公共事件的研發(fā)預(yù)案,以便于在突發(fā)公共事件暴發(fā)時能快速甄別研發(fā)機構(gòu)的能力類型和研發(fā)質(zhì)量。
關(guān)鍵詞:突發(fā)公共事件;研發(fā)質(zhì)量;項目補貼;不對稱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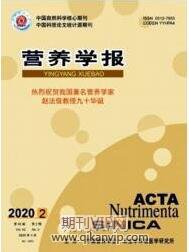
一、引言
在突發(fā)公共事件暴發(fā)時,應(yīng)急領(lǐng)域的研究和發(fā)展活動(R&D)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在巨大的市場利益和社會效益引導(dǎo)下,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yè)在內(nèi)的各類機構(gòu)都會積極開展有關(guān)突發(fā)事件防控的應(yīng)急研發(fā)活動。但是,由于突發(fā)性公共事件往往是由不明原因引發(fā)的,因此,盡管應(yīng)急研發(fā)活動面臨著比較小的市場不確定性,但通常需要承擔(dān)較大的技術(shù)風(fēng)險和技術(shù)不確定性,研發(fā)活動遭遇失敗的可能性比較大。因此,為盡快篩選和開發(fā)有效方案,中央和地方各級部門通常會啟動應(yīng)急研發(fā)項目,對相關(guān)研發(fā)活動給予補貼支持。但是,公共管理者在發(fā)放應(yīng)急研發(fā)補貼時會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由于大量研發(fā)方案和技術(shù)路線都會申請公共管理者的立項資助,在這些研發(fā)活動中,部分高質(zhì)量的技術(shù)路線可能會順利得到資助,而部分研發(fā)機構(gòu)盡管只能做出質(zhì)量低下的產(chǎn)品和方案,也有可能通過釋放虛假的“能力類型”信號而獲得研發(fā)補貼,這就可能導(dǎo)致政府研發(fā)補貼產(chǎn)生“激勵扭曲”問題,從而降低應(yīng)急研發(fā)的質(zhì)量。那么,政府的研發(fā)資助應(yīng)如何在這些項目申請中進行甄別,以選擇最有效的研發(fā)方案呢?研發(fā)主體又將采取什么樣的措施爭取研發(fā)補貼以最大化其收益呢?合理地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能夠揭示突發(fā)公共事件中突發(fā)性研發(fā)活動的特征,同時也有助于提高研發(fā)補貼效率,并為優(yōu)化完善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機制提供理論依據(jù)。以上,就構(gòu)成了本文的創(chuàng)作初衷。
突發(fā)公共事件領(lǐng)域的研發(fā)活動具有正的外部性,研發(fā)機構(gòu)很難完全獲得研發(fā)活動帶來的全部收益,同時,由于研發(fā)活動面臨著技術(shù)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公共管理者通常會對突發(fā)公共事件領(lǐng)域的研發(fā)活動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既可以采取事前資金資助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事后稅收減免的方式來進行。對于突發(fā)公共事件領(lǐng)域的研發(fā)活動來說,政府更多的是在日常或突發(fā)公共事件出現(xiàn)時,采用設(shè)立研發(fā)項目的方式對研發(fā)機構(gòu)進行補貼的(李黎力,2020)。但是,政府研發(fā)補貼的效率往往受到很多質(zhì)疑,從既有文獻來看,理論上有關(guān)政府研發(fā)補貼效率低下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類:
第一,由于在公共管理者和研發(fā)機構(gòu)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政府難以甄別出研發(fā)機構(gòu)的真實類型,也就無法了解研發(fā)機構(gòu)取得研發(fā)成果的可能性(安同良等,2009;周紹東,2014、2019)。鄭月龍、周立新(2020)的研究表明,信息的不完全性會導(dǎo)致政府補貼與機構(gòu)之間的博弈出現(xiàn)完全失靈、部分成功及完全成功3種完美貝葉斯均衡,且均衡主要受到偽裝成本和風(fēng)險成本的影響。彭紅楓(2017)的研究指出,研發(fā)機構(gòu)會通過釋放信號表明自己的研發(fā)能力,他將信號分為正向信號和反向信號,反向信號又根據(jù)不確定性的高低分為真信號和偽信號,政府與研發(fā)機構(gòu)之間的信號博弈又會增加政府甄別機構(gòu)能力類型的難度。
第二,研發(fā)補貼方式和企業(yè)特征也會影響政府研發(fā)補貼政策的激勵效果。政府若因甄別不當對不同類型的企業(yè)采用錯位的“扶弱”或“補強”的補貼政策,則會對企業(yè)績效提升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同時,政府事前補貼、直接補貼和事后補貼、間接補貼對企業(yè)績效激勵作用也有區(qū)別,在于激勵作用是僅限于當期還是具有滯后延伸性(龔毓燁,2019;鄧悅等,2019)。張雅勤、高倩(2018),孫曉華等(2017)的研究表明,政府研發(fā)補貼對企業(yè)績效的效應(yīng)因企業(yè)特征,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所有權(quán)性質(zhì)等不同而存在著差異,例如,國有企業(yè)因享受的優(yōu)惠政策傾斜和需要擔(dān)負的社會責(zé)任,政府研發(fā)補貼當期的促進作用效應(yīng)明顯大于民營企業(yè),但由于特殊的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和預(yù)算軟約束等原因,缺乏擴大研發(fā)投入的動力,同時,民營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績效與政府研發(fā)補貼強度之間存在著門檻效應(yīng)。
第三,政府研發(fā)補貼還有可能扭曲市場激勵機制,形成對微觀主體研發(fā)投入的“擠出效應(yīng)”。公共管理者在分配補貼資金時,承受著避免浪費的巨大壓力,可能會傾向于將補貼投向具有更大成功預(yù)期、高資本回報率的研發(fā)機構(gòu)或項目,而這些研發(fā)機構(gòu)本身就已經(jīng)對研發(fā)項目進行了較高額度的研發(fā)投入,政府的研發(fā)補貼可能是多余的,換言之,有可能會發(fā)生政府研發(fā)補貼對研發(fā)機構(gòu)自身研發(fā)投入的“擠出效應(yīng)”(Lach,2000;鄧悅,2014)。既有文獻還對造成研發(fā)補貼效率低下的原因進行了實證研究,國外研究中,Wallsten(2000)發(fā)現(xiàn)政府資助擠出了企業(yè)自身的R&D花費,資助可能使得企業(yè)保持原有的研發(fā)強度,也即存在擠出效應(yīng)。Hussinger(2008)認為補貼與企業(yè)研發(fā)強度之間呈現(xiàn)出U型關(guān)系,在一定閾值之前,研發(fā)補貼具有擠出效應(yīng)。Catozzella and Vivarelli(2011)發(fā)現(xiàn),企業(yè)創(chuàng)新生產(chǎn)率與政府補貼負相關(guān),得到政府補貼的企業(yè)僅僅通過提高他們的創(chuàng)新支出而耗盡了自己的優(yōu)勢。但在國內(nèi)研究中,李平、王春暉(2010)的研究表明中國政府研發(fā)資助并不會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投入產(chǎn)生擠出效應(yīng)。章元等(2018)的研究則指出,由于政府與企業(yè)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補貼可能會流向已經(jīng)開始投資并且成功概率較高的項目,進而有可能擠出企業(yè)原本計劃的創(chuàng)新投入。同時,他將研發(fā)細分為內(nèi)涵式的自主創(chuàng)新,以及外延式的購買或引進其他企業(yè)研發(fā)的新技術(shù),從而指出政府補貼存在“擠出效應(yīng)”,即被補貼企業(yè)的自主研發(fā)動力明顯下降,而購買引進新技術(shù)的動力顯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