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méi)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méi)有后顧之憂
來(lái)源:期刊VIP網(wǎng)所屬分類:綜合論文時(shí)間:瀏覽:次
摘 要:文道關(guān)系是歷代文論家關(guān)注的核心議題,其中最著名的是觀點(diǎn)是“明道”“貫道”和“載道”三種學(xué)說(shuō),其中“文以載道”是要通過(guò)“文”來(lái)抵達(dá)道的境界,但“載”具有親在性和直接性,這就為文即道或道即文的提倡者以充分的理由。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藝的形象性、物質(zhì)性、可感性和民間性使藝文具備了向上躍升的精神空間,道范疇的形上性和神秘性也適應(yīng)了藝術(shù)的這一追求從而成為其構(gòu)筑理論的核心目標(biāo)。“明道”和“貫道”雖然也強(qiáng)調(diào)“文”的目的是“道”,但缺少“承載”的莊重感和儀式感,而逐步淡出人們的視界。
關(guān)鍵詞:文以載道;藝術(shù)智慧;價(ji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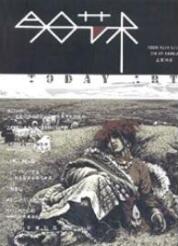
《今日藝術(shù)》國(guó)畫,顧名思義,即表現(xiàn)一國(guó)民精神之繪畫,它將本國(guó)社會(huì)意識(shí)形念之主流用繪畫語(yǔ)言狀述在特種材質(zhì)上,從而達(dá)到一種成教化、助人倫、悅目暢神的目的。
道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藝追求的終極目標(biāo),藝術(shù)家在追求文藝技巧的提升過(guò)程中總是把文藝的精神性內(nèi)容歸結(jié)為對(duì)道的追求,他們?cè)噲D超越文藝的器物層面和技巧層面直達(dá)最高境界。道的崇高性和神秘性不僅適應(yīng)了傳統(tǒng)藝人構(gòu)建其身份認(rèn)同的需要同時(shí)也適合了士人階層向上流動(dòng)的需要。這種以道為核心的理論表述實(shí)質(zhì)就是藝術(shù)家和士人階層(知識(shí)者階層)的話語(yǔ)共謀,以此來(lái)表達(dá)他們對(duì)真理的占有和自我身份的認(rèn)同。清代晚期的劉熙載索性把藝的本性總結(jié)成“藝者,道之形也。”[1]其實(shí),傳統(tǒng)藝術(shù)的“藝即道”和“道即藝”是對(duì)藝術(shù)的精神性和道的可感性的追求,這正如豪澤爾所說(shuō)“它既追求不可見的靈魂,又追求可見、可接觸、可感覺的靈魂的軀殼。藝術(shù)形式就是這兩種追求的結(jié)果。”[2]重道輕藝和重藝輕道都不適合建設(shè)新的文藝,道與藝的有機(jī)結(jié)合才是藝術(shù)健康發(fā)展的必由之路。道藝如何結(jié)合,梳理藝術(shù)理論史中的道藝關(guān)系,也許能為我們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助益。
“詩(shī)言志”或“詩(shī)緣情”是詩(shī)歌最著名的理論,“文以載道”則是散文最為顯赫的理論表述。“文以載道”也是被人誤解最深的一個(gè)理論。先秦時(shí)期,文和道關(guān)系由統(tǒng)一逐步走向分立。
劉勰在《文心雕龍》開篇即言:“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行文至最后曰:“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紀(jì)昀評(píng)之曰:“此即載道之說(shuō)。”“文以載道,明其當(dāng)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shí)其本乃不逐其末。”[3]文“原于道”,簡(jiǎn)稱“原道”。這里紀(jì)昀首次認(rèn)定“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為“載道之說(shuō)”。孫怡讓疏云:“彥和所稱之道,自指圣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徵圣》《宗經(jīng)》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結(jié)合紀(jì)昀的“評(píng)”和孫怡讓的“疏”我們可以知道,劉勰的《原道》重點(diǎn)論述了文起源于“自然之道”,至于“文”是否“載”“道”?作者清楚地說(shuō)是“明道”,而非“載道”。
從整個(gè)篇章的文脈來(lái)看,劉勰極為重視為文的自然之道,這里的“明道”的主體是“圣”,因此不能說(shuō)是他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命題。劉勰在此的理論貢獻(xiàn)并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文以載道”或“文以明道”的命題,而是他看到了文和道的緊密關(guān)系。“文”乃自然之文,“道”乃自然之道。至于文是否可以“載”道,是否可以“明”道,則要看文是否是從天地自然之道中流出,道是否得文之“心”。
紀(jì)昀的“此載道之說(shuō)”和孫怡讓的“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說(shuō)明他們都受到了宋明理學(xué)的“文以載道”理論的影響,也可能是他們理學(xué)的“載道”精神過(guò)度投射所致。《文心雕龍》的《原道》篇雖然沒(méi)有提出“文以載道”的命題,但不是說(shuō)它沒(méi)有這方面的思想,它是以“文”和“道”的關(guān)系為核心展開論述的。可以說(shuō)“文道”是“文質(zhì)”“文氣”和“文德”諸說(shuō)的合理發(fā)展。孔子從培養(yǎng)“文質(zhì)彬彬”的君子出發(fā),提出了文質(zhì)和諧發(fā)展的理論,他的“思無(wú)邪”的詩(shī)教是文以載道思想的萌芽。東漢末年在氣論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進(jìn)而肯定了文的永恒價(jià)值。作為統(tǒng)治階層的曹丕當(dāng)然要重視文的“經(jīng)國(guó)”的政治功用,但他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具體的現(xiàn)實(shí)政治和個(gè)人的“榮樂(lè)”和“飛馳之勢(shì)”,從而使文成為“美則愛,愛則傳”[4]的“不朽之盛事”和“無(wú)窮之聲名”。
《文心雕龍》中的氣論思想受到曹丕的影響是無(wú)疑的,曹丕的“氣”主要是針對(duì)“文”創(chuàng)作的主體而言的,發(fā)展到劉勰時(shí),“氣”則成為貫穿創(chuàng)作、作品和欣賞的統(tǒng)一性元素。所謂“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太極”即天地未形成前的原始混沌之氣,這實(shí)質(zhì)上是把文章的起源推到了神秘的不可知的領(lǐng)域。王元化認(rèn)為《文心雕龍》的宗旨是原道、征圣、宗經(jīng);他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中的“道”“圣”“文”雖然各為三,實(shí)則同指儒學(xué)。[5]如果真是這樣,劉勰的藝術(shù)本體論思想就沒(méi)有什么新鮮的地方,只是沿用了兩漢時(shí)期的經(jīng)學(xué)思想而已。
但《文心雕龍》的可貴之處是它從“文”產(chǎn)生的究極之地來(lái)闡釋“文”和“道”的關(guān)系,他也從“道”的恒在意義上來(lái)表明心志。例如他在《雜文》中寫道:“身挫憑乎道勝,……此立本之大要也。”[6]因此可見劉勰的“道”并非僅限于現(xiàn)實(shí)政治的成敗之道,而是超越其上的“恒道”。他所說(shuō)的“文”也并非僅指載現(xiàn)實(shí)政治之“文”,也指包括“天地并生”的“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的“大文”。由此可見,劉勰的“文從道出”或“圣因文而明道”就具備著“包前孕后”的理論原型的質(zhì)素。
“文從道出”和“因文而明道”發(fā)展到唐宋時(shí)期,就成為“文以載道”和“文以明道”的理論命題。對(duì)于“文以載道”,如果去除其封建僵化的思想內(nèi)容,擯棄其純粹工具論的思想,把它理解為一種形而上的文論原型,它就是中國(guó)古代一個(gè)十分光輝的命題。“明道”雖然在先秦儒家和道家均已明確提出,但基本上是哲學(xué)和倫理學(xué)的概念。
先秦諸子均有自己的“明道”觀念,但“文”與“道”或“藝”與“道”是一種較為松散的關(guān)系,這時(shí)的“明道”觀念多是圣人、君子、隱逸之士的政治哲學(xué)或統(tǒng)治者的政治之術(shù)。這一時(shí)期的“文”和“質(zhì)”的關(guān)系明顯比“藝”和“道”的關(guān)系要緊密。因?yàn)閺氖滤囆g(shù)的多是處于“吾不試”境遇的人,孔子所言的“志于道”排在第一,“游于藝”只能處于末位,這和《樂(lè)記》中所言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情況相同。
而“詩(shī)”和“文”的情況則不同,詩(shī)文以文字為材料形式,它們具備詮釋政權(quán)合法性的天然地位,不管是甲骨文還是鐘鼎銘文,都有著溝通天地的神圣功能。殷商時(shí)期重要的巫師甚至可以掌握著話語(yǔ)權(quán),決斷戰(zhàn)爭(zhēng)、祭祀等現(xiàn)實(shí)的重大事情,他們靠的就是其熟練掌握的甲骨文這個(gè)象征性的媒介。而鐘鼎銘文則是紀(jì)念碑性的文字,這種金屬材料和文字的結(jié)合把貴金屬的象征性和文字的隱喻功能發(fā)揮到極致,后代的諸如秦泰山刻石基本上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
這一時(shí)期的“文”是政治之文,“道”是政治之道,“文”和“道”是合一的。所謂“學(xué)在官府”的“王官文化”是春秋以前的主要文化類型。春秋時(shí)代后以孔子為代表的私學(xué)興起,文化的高度壟斷性開始松動(dòng),文化開始向下層流動(dòng),從而造成士階層的形成。士階層的形成使文和道逐步分裂為二,統(tǒng)治階級(jí)話語(yǔ)權(quán)的絕對(duì)性和權(quán)威性開始動(dòng)搖,此為孟子所言的“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7]的時(shí)代。這時(shí),楊朱墨翟之學(xué)盈于天下,自然也是極端混亂和價(jià)值重構(gòu)的時(shí)代。殷商時(shí)期的以《詩(shī)經(jīng)·大雅》為代表的“文”和以青銅器為象征的國(guó)家政權(quán)的“道”在風(fēng)格上是一致的,這也是文道合一的癥候。
及至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百家爭(zhēng)鳴”“處士橫議”“諸侯放恣”,代之而起的是“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8]。價(jià)值的一元論逐步為價(jià)值多元論所取代,這也是春秋戰(zhàn)國(guó)藝術(shù)繁榮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天道的觀念式微,人道觀念興起,人的終極關(guān)懷由天上落到人間。《莊子·天下》篇描述了“道術(shù)”分裂、“方術(shù)”興起的狀況: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wàn)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shù),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yùn)無(wú)乎不在。其明而在數(shù)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shī)》《書》《禮》《樂(lè)》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shī)》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lè)》以道和,《易》以道陰陽(yáng),《春秋》以道名分。其數(shù)散于天下而設(shè)于中國(guó)者,百家之學(xué)時(shí)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zhǎng),時(shí)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wàn)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9]
《天下》篇所描述的這種狀況顯示了歷史的巨大進(jìn)步,殷商時(shí)期所謂統(tǒng)一的“文”和統(tǒng)一的“道”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美其美”的“一曲之士”的“方術(shù)”。這種片面的深刻相對(duì)于混沌的文道合一來(lái)說(shuō)是一種進(jìn)步,道家的“判”“析”“察”的學(xué)術(shù)精神在隨后的歷史中沒(méi)有發(fā)展出“求真”的科學(xué)精神,不期然卻誤入了自然美的花園。
究其原因可能是復(fù)雜的,但從《天下》篇來(lái)看,它的“分析”精神也就是“與物宛轉(zhuǎn)”和“常寬于物,不削于人”的藝術(shù)精神,和西方的主客二分的“分析”是大異其趣的。況且這些“術(shù)士”們所追求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也進(jìn)一步阻礙了人們對(duì)物質(zhì)世界的更深層次的物理探究。中國(guó)古代的全部學(xué)術(shù)就流于內(nèi)在的“修養(yǎng)”和外在的“經(jīng)世”。 “‘內(nèi)圣外王之道’一語(yǔ),包舉中國(guó)學(xué)術(shù)之全部。
中國(guó)學(xué)術(shù),非如歐洲哲學(xué)專以愛智為動(dòng)機(jī),探索宇宙體相以為娛樂(lè)。其旨?xì)w在于內(nèi)足以資修養(yǎng)而外足以經(jīng)世”梁?jiǎn)⒊骸读簡(jiǎn)⒊?第八冊(cè)),北京出版社,1999:4676.秦觀對(duì)這種道術(shù)分裂也有著相似的認(rèn)知,他在《韓愈論》中論及這一情況:“臣聞先王之時(shí),一道德,同風(fēng)俗,士大夫無(wú)意于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后世道術(shù)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為文。故自周衰以來(lái),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起私智,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10]統(tǒng)一的“道”不存在了,繼之而起的是各言自家之道。諸子百家為了爭(zhēng)奪各自的“象征性資本”均站在自己的立場(chǎng)上爭(zhēng)奪話語(yǔ)權(quán),指摘對(duì)方的局限。
處于顯學(xué)地位的學(xué)派也非鐵板一塊。據(jù)歷史記載,“孔子歿后,儒家一分為八”,是否分為八家筆者不去深究,但可以相信的是儒家自孔子后它的內(nèi)部也存在諸多不同的甚至對(duì)立的觀點(diǎn)。可見,即使是原始儒家內(nèi)部對(duì)“道”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解。這種混亂和差異的“道”不僅顯得晦暗不明,甚至有被遮蔽的危險(xiǎn),這就自然就導(dǎo)致“明道”觀念的出現(xiàn)。三皇五帝的時(shí)代是公認(rèn)的“大道至明”的時(shí)代,不需要刻意去“明道”,春秋戰(zhàn)國(guó)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時(shí)代,因此“明道”就成為有雄心的傳統(tǒng)知識(shí)分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