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摘要:在“通州建總集團有限公司與內蒙古興華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上訴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當事人之間的以物抵債協議構成新債清償,并以新債清償的理論作為支持一方當事人請求的裁判依據。這一裁判思路在法源上是值得商榷的,通過合同解釋和類推適用的方式也可以得出同樣的裁判結果。代物清償與代物清償契約從概念上應予以嚴格區分,代物清償契約的履行方構成代物清償。新債清償與債之更改從不同的角度確立了代物清償契約的同一解釋規則。以物抵債協議的性質,應根據其成立后的履行狀態和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內容來判斷是否構成代物清償、新債清償或債之更改。
關鍵詞:以物抵債;代物清償;新債清償;債的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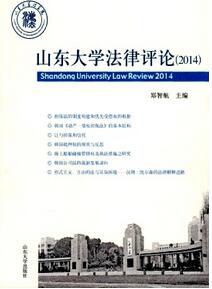
一、基本案情和主要裁判思路
(一)案件概要
2005年6月28日,內蒙古興華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興華公司”)與通州建總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通州建總”)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興華公司將呼和浩特市供水大廈(以下簡稱“供水大廈”)工程的施工任務發包給通州建總。合同簽訂后,通州建總進場施工完畢,興華公司于2010年底投入使用。2012年1月13日,興華公司與通州建總呼和浩特分公司第二工程處簽訂《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一份,約定用興華公司的供水大廈樓盤A座9層房屋抵頂部分工程款1095萬元。但在《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簽訂后,興華公司曾欲變更協議書約定的抵債房屋的位置,未得到通州建總同意。其后,興華公司既未及時主動向通州建總交付約定的抵債房屋,也未恢復對舊債務的履行即未向通州建總支付相應的工程欠款。截至二審,供水大廈A座9層尚未辦理房屋所有權首次登記及任何轉移登記。由于興華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工程欠款,通州建總向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訴請興華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利息和違約金。一審判決興華公司向通州建總給付工程款26004559.35元及其利息,興華公司不服提起上訴,請求對一審判決進行部分撤銷和變更。
(二)關鍵爭議點
在二審中,除材料價值、利息和工程款計算等問題外,最關鍵的爭議點在于《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約定的供水大廈A座9層抵頂工程款是否應計入已付工程款中的問題。興華公司認為,對于《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雙方既未解除,也未被法院確認無效或撤銷,故對雙方均有約束力,該房屋已經屬于通州建總。因此,該1095萬元應當認定為興華公司已付工程款。通州建總則認為,興華公司在一審中出示《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的目的在于證明其有履行付款義務的意思,而非主張用以抵頂工程款,并且該協議并未履行,不可能抵頂已付工程款。
(三)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基本正確,一審法院認定并判令興華公司應向通州建總支付相應的工程欠款,并無不當,僅在部分欠付工程款利息起算時間問題的處理上存在不當,應予糾正。
(四)關鍵爭議點的主要裁判理由
本案的關鍵爭議點是涉案《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約定的供水大廈A座9層房屋抵頂工程款金額是否應計入已付工程款中。也就是說,舊債(相應金額的工程款債務)在《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簽訂時是否已經消滅?如果《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之訂立并未消滅舊債,則興華公司不履行新債(交付抵頂房屋的債務)時,通州建總方可否請求興華公司履行舊債?易言之,這涉及兩個問題:第一,以物抵債協議生效后舊債是否消滅?第二,新債不履行時,債權人是否可以主張舊債權?對于上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提出了如下論證理由:
首先,以物抵債系債務清償的方式之一,是當事人之間對于如何清償債務做出的安排,故對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履行等問題的認定,應以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為基本原則。一般而言,除當事人明確約定外,當事人于債務清償期屆滿后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并不以債權人現實地受領抵債物或取得抵債物所有權、使用權等財產權利為成立或生效要件。只要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實,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同即為有效。本案中,《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情形,故該協議有效。
其次,當事人于債務清償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可能構成債的更改,即成立新債,同時消滅舊債;亦可能屬于新債清償,即成立新債,與舊債并存。基于保護債權的理念,債的更改一般需有當事人明確消滅舊債的合意,否則,當事人于債務清償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性質一般應為新債清償。換言之,債務清償期屆滿后,債權人與債務人所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如未約定消滅原有的金錢給付債務,應認定系雙方當事人另行增加一種清償債務的履行方式,而非原金錢給付債務的消滅。本案中,雙方當事人簽訂了《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但并未約定因此而消滅相應金額的工程款債務,故該協議在性質上應屬于新債清償協議。
再次,所謂清償,是指依照債之本旨實現債務內容的給付行為,其本意在于按約履行。若債務人未實際履行以物抵債協議,則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問的舊債并未消滅。也就是說,在新債清償,舊債于新債履行之前并不消滅,舊債和新債處于并存的狀態;在新債合法有效并得以履行完畢后,因完成了債務清償義務,舊債才歸于消滅。在本案中,供水大廈A座9層房屋既未交付通州建總實際占有使用,亦未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于通州建總名下,興華公司并未履行《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約定的義務,故通州建總對于該協議書約定的擬以房抵頂的相應工程款債權并未消滅。
最后,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據此,債務人于債務已屆清償期時,應依約按時足額清償債務。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達成以物抵債協議、新債與舊債并存時,確定債權人應通過主張新債抑或舊債履行以實現債權,亦應以此作為出發點和立足點。若新債屆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債協議目的不能實現的,債權人有權請求債務人履行舊債;而且,該請求權的行使并不以以物抵債協議無效、被撤銷或者被解除為前提。
綜上所述,興華公司并未履行《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約定的義務,其行為有違誠實信用原則,通州建總簽訂《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的目的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通州建總有權請求興華公司直接給付工程欠款。
(五)本案裁判的主要思路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裁判的主要思路可以歸納如下:
1.《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屬于以物抵債協議,除當事人明確約定外,當事人于債務清償期屆滿后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屬于諾成合同。2.當事人于債務清償期屆滿后達成的生效以物抵債協議,可能構成債的更改或新債清償。債的更改一般需有當事人明確消滅舊債的合意,否則,當事人于債務清償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性質一般應為新債清償。據此,本案的《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構成新債清償。3.新債清償的效力在于,舊債于新債履行之前不消滅,舊債和新債處于并存的狀態;在新債合法有效并得以履行完畢后,因完成了債務清償義務,舊債才歸于消滅。本案中,興華公司并未按照《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約定履行新債,故興華公司對通州建總的1095萬元債務并未消滅。4.若新債屆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債協議目的不能實現的,債權人有權請求債務人履行舊債。因此,通州建總有權請求興華公司履行舊債。
二、本案的請求權基礎與法律適用之檢討
法官在民事案件裁判過程中,必須裁判雙方當事人之問關于一項由原告在訴訟中提出的“請求權”爭議,但應“受到具有約束力的現有法律規范的嚴格約束”。在實證法的前提下,法官在裁判案件中需要按照“確定法效果的三段論法”來進行裁判。在此過程中,可供支持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有所主張的法律規范,被稱為“請求權基礎(Anspruchsgrundlage)”。在對系爭案件進行裁判時,法官應首先按照既有實體法規范進行法律解釋、推理來尋求請求權基礎,除非因法律漏洞的存在導致可供直接適用之請求權基礎缺失,方能通過類推適用、目的性限縮(擴張)等方法來進行請求權基礎的發現或創設工作。就本案而言,本文并不質疑其裁判結果,但對其裁判思路存有如下疑問:在本案裁判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援引了新債清償、債的更改的概念和理論,并將新債清償的相關理論作為支持通州建總請求給付工程欠款主張的主要依據。這樣的做法雖然體現了法官在裁判過程中越來越重視說理,但新債清償并非我國制定法上的制度,法院在本案中引用新債清償的理論,是否有“司法權過于擴張之嫌疑”?
在本案中,如果當事人之間僅存在一個給付工程欠款的合同,則通州建總請求支付欠款的請求權基礎就會非常明晰:通州建總與興華公司事前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屬于我國《合同法》明確規定的有名合同,應先依據《合同法》中有名合同的相關規定尋找請求權基礎,請求權基礎應為《合同法》第286條。但由于當事人之間事后簽訂的《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為無名合同,通州建總請求興華公司交付房屋的請求權基礎應為《合同法》第8條和第60條第1款。難辦的是,通州建總在簽訂了《房屋抵頂工程款協議書》后再請求履行舊債的請求權基礎在現行立法中并沒有直接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為了裁判之需要,引用新債清償與債之更改的區分標準、新債清償的效力作為裁判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將通州建總主張舊債的請求基礎由《合同法》第286條進行了“規范”的擴張。本文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國直接引用學說或法理作為裁判依據缺乏法源基礎。如果在裁判過程中必須要引用學說或法理作為依據,其前提是有法律的明確“授權”,即法理應為法源。在本案判決下達之時,當時仍舊生效的《民法通則》僅在第6條規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應當遵守國家政策。”在《合同法》的法域下,也未授予法官在解決合同爭議時可直接適用學說和法理。如果法院意圖引用學說增強判決的說理性,理想的做法應當是在明確請求權基礎和法律適用依據的前提下,將學說作為一種佐證。
第二,直接引用學說或法理作為裁判依據超越了法官對法律的裁判解釋權。我們并不否認,法官在個案審判中可以行使對法律的裁判解釋權,法官在其判決書中所做的解釋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也是有權解釋。但這種有權解釋僅對個案有效,并不具有普遍約束力。法官行使裁判解釋權時,解釋的全部前提條件都必須存在于法律自身之中。法律解釋等同于對法律所包含的思想的重建,前提是可以從法律本身探知這種思想。顯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直接將學說作為裁判依據的裁判模式并非是對法律規范的解釋,因此不屬于法官裁判解釋權的范疇。
第三,立法對本案所涉法律漏洞已預設了填補方式。本案法官采用學說進行裁判,顯屬將本案爭議問題視為法律未規定之漏洞下的無奈之舉。“法律適用者必須做出判決”,故即使法律存在漏洞,法官也必須進行裁判。法律漏洞分為有意識的漏洞和無意識的漏洞,如果立法者希望司法做出規定,那就是有意識的漏洞。立法者對待有意識的漏洞,往往采用由法律明文授權法院將某案型之法律規定適用到另一個類似的案型上之“授權式類推適用”的方式,以避免煩瑣的重復規定。也就是說,針對有意識的漏洞,法官應先行識別法律是否規定了授權式類推適用的條款。就新債清償而言,在《合同法》起草過程中,1995年由專家起草的《合同法(建議草案)》第七章第二節第121條實際上進行了規定。但在正式通過的《合同法》文本中,新債清償被刪除。刪除的立法理由在于:合同的清償與履行是從不同的方面對同一行為的反映,為避免法律規定過于繁雜,對清償的具體內容沒必要單獨規定。可見,立法者認為依據現行法之規定,亦足以起到與已刪除條款相同的規范效果。以物抵債協議為無名合同,從我國《合同法》的立法來看,第124條、第174條都屬于針對無名合同采取授權式類推適用的規定。因此,在系爭無名合同的當事人對爭議點沒先行約定時,如不能通過合同解釋的方式來解決爭議,應根據無名合同的性質選擇性類推適用《合同法》第124條或第174條。針對本案中的法律漏洞,立法者事實上已為法官預設了法定的填補方式。因此,即使本案爭議問題無直接用以裁判的條款屬于存在法律漏洞,本案法官填補漏洞方式的合法性也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