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在目前有關民事司法新管理應用措施有哪些呢,要如何來促進現在拍賣的新管理條例制度呢?本文是一篇法學論文。雖然拍賣公司作為委托拍賣的直接操作者,其自身行業固有的問題是直接導致了司法拍賣目前的窘境的一個原因,但考慮到拍賣公司在我國發展時間還不長,行業規范也比較模糊,加之人民法院之前一直在適用變賣程序,對拍賣程序并不熟悉,短時間將兩個誕生和發展都不成熟的制度融合在一起,期望達到限制司法權力濫用進而預防司法腐敗的目的是非常困難的。
摘要:司法拍賣是以人民法院對有關財產合法有效的司法控制為前提,以換價為中介,以債權清償(即執行)為目的的一種司法行為。長久以來委托拍賣一直是司法拍賣的實踐操作模式,但這一模式卻因各種丑聞的頻繁爆出而廣受社會公眾的質疑和噓聲。面對民意,各地方法院也在有意識的尋求改革的突破口,追求一種更為合理有效的發展方式,并逐漸演變出了三種主流的司法拍賣模式,即保守的“上海模式”、創新的“重慶模式”以及激進的“浙江模式”。這三種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處,但卻各有側重,引發的爭議甚至是沖突,也好似“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四面開花。有鑒于此,本文希望通過對委托拍賣和網絡司法拍賣的應用的具體操作程序進行分析,對比出三種模式在程序操作上的優缺點,并以此為基礎探索出一種符合我國當下國情與司法環境的司法拍賣模式。
關鍵詞:民事法學,司法管理,法學論文范例
一、 委托拍賣與網絡拍賣之現狀
自浙江法院于20xx年7月首次與淘寶網上聯合推出網絡司法拍賣以來,網絡司法拍賣這個新鮮詞匯瞬間就充斥著各類媒體的新聞版面,而根據一份網絡調查報告顯示,有94%的網友對浙江法院法院這次選擇在淘寶上進行司法拍賣表示贊同,有88%的網友表示此舉可以在全國范圍推廣,還有近64%的網友明確表示會考慮參與網絡司法拍賣。
法學論文:《法學天地》,《法學天地》1986年創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雙百方針”,理論聯系實際,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和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進學院教學、科研工作的發展,為教育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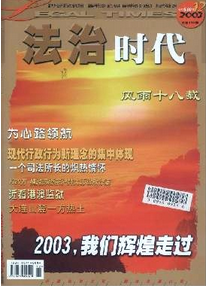
與之相反的則是確立自20世紀90年代末《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的委托拍賣制度,不斷的被曝光出各種各樣因人為因素而發生的大量違法違紀行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分管執行工作的原副院長張弢、執行庭原庭長烏小青案,都因涉嫌在司法拍賣中違規操作而落馬。根據統計,全國民商事案件有近6成生效判決會進入執行程序,在進入執行程序的有可供執行財產案件中, 80%左右的財產是房產、地產、車輛等需要經過司法處置來實現變現的財產,而全國法院因司法拍賣而落馬的法官而占法院系統違法違紀人數的70%。
兩相對比,司法拍賣改革似乎已經迫在眉睫,網絡司法拍賣或許可以代替委托拍賣成為司法拍賣的一條新的康莊大道。然而委托拍賣真的就一定是毫無價值?網絡司法拍賣就一定能取而代之?筆者以為即便目前的網絡司法拍賣持續火爆,但這并不能說明網絡司法拍賣就一定要全盤替換傳統的委托拍賣,要理順司法拍賣抉擇之路就一定要從委托拍賣之起源開始看起。
二、委托司法拍賣之起源與問題之根源
事實上、作為飽受民眾質疑和不滿的傳統司法拍賣運行模式的委托拍賣其實在設立之初就是為了解決法院執行機構的司法腐敗并且規范涉訟財產變價過程而設立的。但為何當時被頗受期待的“防火墻”卻成為了司法腐敗的多發之地?
自1958年以來,隨著拍賣行在中國大陸的消失,司法拍賣程序也隨之銷聲匿跡,期間新中國僅在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法院的強制拍賣權,在確立了強制拍賣的合法“名分”的前提下并未涉及強制拍賣的性質和效力,導致各地法院仍然通過變賣這一方便且簡便易行的方式來進行資產處置。【3】但是實際上變賣屬于一種簡便經濟的變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的實現涉訴財產應有的價值,在保護申請人以及被執行人利益的合法權益上略有欠缺,而且作為變賣的組織單位,人民法院在操作中也難免發生貪腐現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1998年的《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中首次明確了委托拍賣這一制度。
不可否認的是,最高院實際上是在缺乏相應的實踐的基礎上確立了委托拍賣的制度,因此由于該制度在初期的倉促試行,導致委托拍賣一直沒有沒有形成一個整體的框架,直到20xx年制定《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之前,司法拍賣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各地法院亂象頻生的重災區,絕大數的財產變價過程缺乏有效的規制,出現了拍賣公司高收費高傭金、雙向收費等一系列問題,這加劇了輿論以及民眾對司法拍賣制度的批評和懷疑,委托拍賣以及站在第一線的拍賣公司成為了眾矢之的。
另外通過委托拍賣行來進行拍賣也會產生一定的弊端,據商務部的“全國拍賣行業管理信息系統”數據顯示:截止20xx年底中國內地拍賣企業共有5860家,數量較20xx年新增374家,而行業人數總數突破6萬,過快的發展速度導致目前拍賣行業的經營狀況中存在著五成盈利、三成持平、兩成虧損的狀況,生存境十分惡劣【4】。而從業務來源來看,根據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發布的《2013年上半年行業經營情況簡歷》指出,在相關的房產車輛等拍賣的主要業務中,法院委托拍賣仍然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各種原因導致拍賣公司迫于生存的壓力,必須花費更多的精力和手段放在獲取法院司法拍賣委托上(進入法院制定的名冊,并獲得更多的司法拍賣案件),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催生了大量的利益分配【5】以及其他形式的司法腐敗的現象。
應當承認,委托拍賣的實質其實就是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過程,即通過犧牲涉訟財產的部分價值,通過商業性的運作,縮小司法權力的涉及范圍,來排除個別司法主體透過司法拍賣謀求不正當利益。這也就是說立法者的本意是期望通過司法拍賣的市場化運作竭力避免司法權力對司法拍賣的過度干涉,降低司法腐敗幾率,用以最終實現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并保持司法機關的純潔性。然而目前我國并沒有專門的民事強制法,關于強制執行的相關規定散見于《民事訴訟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當中,并且這其中有關于司法拍賣的條文多是對司法拍賣的流程的規定,忽視了對司法拍賣的本質以及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的規制,在委托拍賣施行以來,法院司法鑒定部門、拍賣公司、第三方產權交易所以及網絡平臺等先后介入司法拍賣,這必然導致司法拍賣參與各方的混亂,權利以及義務的不對等、不明確以至于形成了司法權在司法拍賣中基本不受約束的事實,實際上在很多時候,拍賣公司成為了司法機關在民眾面前的擋箭牌。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傳統司法拍賣在運行中暴露出來的眾多問題不單單只是拍賣公司一方的問題,缺失的法律規范以及參與司法拍賣主體的復雜性,共同導致了目前的委托拍賣制度陷入了泥潭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