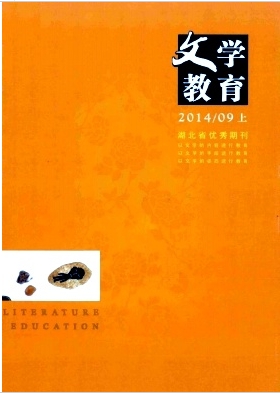《喜福會》描寫了四對母女、八個女人的生活以及命運的一系列故事,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文學論文投稿:探究其中的女性主義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查看。
摘要:譚恩美是美國著名的華裔女作家,她的處女作《喜福會》一經發表即引起轟動,獲得了美國普通讀者和評論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本文從小說的敘事角度和作者對男權主義的批判兩個方面,對《喜福會》進行了女性主義分析,希望藉此能為其他學者研究譚恩美提供新的視角。
關鍵詞:喜福會 譚恩美 女性主義 父權文化 壓迫 反抗
自20世紀 70年代以來,反映 “邊緣文化”的美國華裔文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美國華裔女作家譚恩美憑借其處女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1989)在美國文壇一舉成名。該小說自出版后不斷再版,曾雄踞美國暢銷書榜達八個月之久,并先后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國家圖書批評循環獎及1991年最佳小說獎。國內很多學者對《喜福會》這部小說的評論都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中美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母女之間的關系問題。但筆者認為以上兩個方面并不是《喜福會》的真正主題,他們僅僅為小說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而已。我們不難發現,小說字里行間包含著作者對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所遭受的壓迫所表現出來的同情、憤慨和對種種壓迫的強烈抨擊。本文即從女性主義這一視角來解讀《喜福會》。
一、以女性為中心的寫作手法
《喜福會》描寫了四對母女、八個女人的生活以及命運的一系列故事。盡管這些故事相互交錯,但母親們的故事是發生在中國的,而女兒們的故事則發生在美國。如果說從母親們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舊時女性的命運的話,那么女兒們的故事則代表著現代女性的生活境遇。在這些故事中,女人們登臺做主角,男人們要么不出現,即使出現也僅僅是女人們的陪襯而已。《喜福會》是一部描寫女人的書,是一部為女人而寫的書,并且也是由女人們來完成敘述這一任務的書。
長期以來,男性文本都采用一種以男性為閱讀對象的敘述策略。因此女性形象在文學中,曾一度僅是一種對象性存在和空洞的符號,不是作為主體從正面加以描寫的。譚恩美顛覆了這一寫作傳統,創造了一個以母女關系為基礎,以女性為主的世界。
小說中出現的第一位母親是吳素云,她是喜福會的發起人。在從中國的一個戰區逃難時,她被迫遺棄了自己的雙胞胎女兒,同時戰爭也使她成了寡婦。后來她到了美國,重新嫁人,又有了女兒吳精美。
第二位出場的母親是許安梅,但作者在這部分中講的主要是許安梅母親的故事:丈夫早逝后她又不幸被誘奸,不得已做了別人的四太太。為了讓安梅不再過屈辱和不幸的生活,她在農歷新年前夕服毒自盡。
第三位出場的母親是龔琳達,她兩歲時成為童養媳,結婚后由于丈夫不諳男女之事而備受婆婆刁難,最終憑借自己的聰明設計解除了婚約來到美國。
最后一位出場的母親是英英?圣克萊爾,她善良單純卻嫁給了一個花花公子。當她懷孕時得知她的丈夫從沒對她忠誠過之后,又生氣又傷心,最終打掉了未出生的孩子。
譚恩美精心挑選的母親們的故事,分別代表了舊中國女性最典型的四種婚姻情況:成為寡婦、妾、童養媳以及遇人不淑。許許多多的中國女性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一代一代地生活過來的。她們有苦,有淚,卻無可訴說,無法逃避,在中國典型的父權制文化中她們只能默默承受,把痛苦當作女人的宿命接受下來。
女兒們的故事則與母親們不同,她們生長在美國,擁有經濟上的獨立和人格上的自主。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在經濟上獨立的現代女性,能否真正實現自我。
吳精美是吳素云的女兒,倔強而善良。她認為自己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講都算不上是個成功者,辜負了母親的期望,也一直保持著獨身。在母親去世后,她終于理解了母親的一番苦心,回到大陸找到了自己的雙胞胎姐姐。
羅斯,安梅的女兒,曾經不顧母親的反對和婆婆的種族歧視,堅持嫁給了一個年輕英俊的白人特德。這足以顯示了她的主見,但她卻一直讓特德來決定家中的一切事情。她和丈夫的關系一直都是拯救者與被拯救者、施令者與聽從者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反映了男權文化的特色――男尊女卑、男主動女被動。
琳達的女兒韋弗利自幼爭強好勝,婚姻破裂后與新男友同居。她擔心母親的反對會毀了她和新男友的婚姻,希望能和母親達成諒解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做。
英英的女兒莉娜認為自己在智力、能力等方面都不亞于丈夫,可她在與丈夫哈羅德的婚姻中卻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莉娜追求的是在經濟上與丈夫的絕對平等,無論婚前婚后都和他平攤一切費用。她出主意協助哈羅德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建筑設計公司,并為公司做出很多貢獻,卻僅僅因為她是他的妻子而得不到升職加薪。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兩性平等。
在經歷過婦女解放運動后的美國,女性的生活境遇應該是有所改善的。但正是對這些美國現代女性的描寫,深化了譚恩美的女性主義思想。男權社會滲透于女性意識深層的自我貶低、自我排斥、自我抹殺的傳統觀念,已逐漸內化為她們的集體無意識。譚恩美想說的是:現代女性并沒有實現與男性的平等,她們仍處于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中,只不過形式更加隱蔽罷了。這四對母女的故事,展現了華人女性從傳統到現代的全部生活狀況,抨擊了父權文化對女性的壓迫和摧殘。
二、對男權主義的批判
法國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創始人西蒙?波伏娃曾說過:“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女孩們從孩提時代起就被灌輸這樣一種觀念:她們并不具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和地位,她們僅僅是被剝奪了自主權的、男性的附屬品而已。“父權制文化標準不僅有一種強制性,迫使婦女處于生活的底層,沒有經濟地位和閑暇時間,它還有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婦女長期生活在父權文化的熏陶下,逐漸將這種強制的東西內化為自身的價值取向,社會因之只存在一種價值標準,這便是男性價值標準。”這樣,女性逐漸淪為一種對象性存在,失去了自由意志,成為“第二性”。
男權主義是中美文化中共同存在的問題,小說中的四對母女幾乎都遇到過這樣的問題。舊中國是一個男權至上的社會,社會要求女性扮演富有犧牲精神的賢妻良母的角色,遵守“三從四德”的古訓。琳達遵從父命,到婆家做了童養媳后,一心想的就是認真學做家務事,討得丈夫和婆婆的歡心,不給家族丟臉。她還告訴自己:“天宇是上帝,他的意識高于我的生命。”這樣,琳達完全達到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淪為了為男性生活服務的工具。男權文化的侵蝕性,在于它使女性不僅成為其道德規范的接受者,并且成為其捍衛者。
安梅的外婆因為守寡的女兒遭到強奸而被迫成為姨太太,就將其逐出家門,并斷絕了關系。我們不禁對安梅外婆的這種做法表示疑惑和不解,但頑固的貞操觀念,這一男權社會判斷女性價值的至高標準泯滅了她的母性,使她成為男權主義的幫兇進而去壓迫自己的女兒。英英的奶媽告訴她,女兒家不能問只能聽著,以這種方式把男權主義社會的婦道傳授給她。
女兒們在美國的生活中,也同樣遭遇到了男權主義。當韋弗利在唐人街的公園里找老頭下棋的時候,他們表示不愿意和小女孩玩;當他們看到她能在男人擅長的游戲中表現不俗時很驚訝。莉娜這位獨立自主的職業女性也無法逃脫傳統觀念的影響。“由于是在尊重男性優越地位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她現在仍可能認為應當把男性擺在首位;有時她擔心如果她要求把自己擺在第一位,會毀掉自己的家庭;在堅持自己的權利和謙讓這兩種欲望之間,她左右為難,終于被分裂了。”
莉娜出主意幫助丈夫創辦了公司,答應只做個副手并只拿他工資的七分之一。她幻想用經濟上的忍讓和付出來換取丈夫的感情的做法,結果卻令她逐漸失去了是非觀念和自我意識,婚姻也岌岌可危。
譚恩美通過這些舊中國女性和美國現代女性的遭遇,向我們揭示了男權主義不但在過去壓迫和摧殘過女性,而且現在它也沒有銷聲匿跡。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的男權主義,需要現代女性用更加清醒的頭腦、更加敏銳的目光去認識和應對。
三、結論
總之,強烈的女性主義思想是《喜福會》的一大突出特點。譚恩美以其華裔女性的獨特視角,通過對深受幾千年封建傳統文化禁錮和壓迫的舊中國女性和新時代美國現代女性的形象塑造,揭露了男權主義的隱蔽性和長期性。在自己創作的小說中,顛覆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書寫傳統,構建了一個女性世界――為女性搭建了一個屬于她們自己的舞臺去展現喜怒哀樂。通過對母女兩代人生活境遇的描寫,譚恩美代表所有的華人女性發出了自己的呼聲,控訴了男權主義對女性的壓迫,給予女性以鼓舞和力量。濃重的女性情懷使我們仿佛聽到了作者發自肺腑的吶喊:“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我為生為女人而感到自豪!”
參考文獻:
[1]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鐵柱譯:《第二性》,中國古籍出版社,1998年
[2] 譚恩美:《喜福會》,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
文學期刊推薦:
《文學教育》是中國學術期刊網(又名中國知網)全文收錄期刊和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收錄期刊,每年有多篇文章被中國人大復印資料等權威期刊全文轉載。為了進一步把這份刊物辦好,從即日起,我們特向全國一切關心文學教育、研究文學教育、從事文學教育的人士約稿,歡迎各位朋友踴躍賜稿,我們一定做到以質取稿,不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