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摘 要:20世紀20年代,中國公學地發展得力于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校董地推動。以梁啟超晚年搭建的“政治—文化”框架為脈絡,主張“教育救國”的基本方針,實現了中國公學的大學升格。但其內質化的學權派系斗爭,最終促成了私立中國公學困境下的“改朝換代”。
關鍵詞:梁啟超 中國公學 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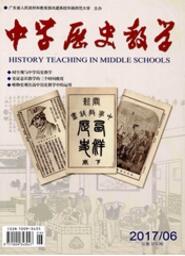
作為近代早期的私立學校之一,中國公學甚少為人所知,但胡適曾評價說,“中國公學的校史,實在可以算作中華民國開國史和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 目前中國學者在對梁啟超與中國公學的考察中,主要以梁啟超的中國公學作為切入點,在中國公學校史的“分段”背景下,凸顯了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與中國公學“政治—文化”的雙向妥協。
梁啟超接掌中國公學
1905年日本政府頒布《關于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引發了中國留日學生的不滿,遂決定回國自辦學校,“以謀造成真國民之資格,真救時之人才也”,并于1906年在上海創立中國公學。當時同在日本的梁啟超在《記東京學界公憤事并述余之意見》一文中認為,日本針對中國留學生的規程“其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國留學生之自由,不過監督此種類之學校,而以圖留學生之利益耳。”反對留日學生沖動返國,且對“中國公學”并不看好。但隨著梁啟超思想活動的轉變,其對中國公學的態度也發生了由關注到加入的轉變。
1.梁啟超思謀社會教育事業
1916年,梁啟超漸生隱退政治之心,認為“作官實亦損人格,易習于懶惰與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頃方謀一二教育事業”(民國五年十月十一日《與嫻兒書》)。并指出“中國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實無庸為諱,非亟從社會教育上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則雖似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與報館記者談話》,《文集》卷五十六頁六),認識到社會教育是國家政治轉型的突破口,“但是自去冬以來,憲法問題、對德外交問題、內閣問題和復辟問題等,都與先生有不可解的問題。”最終還是加入了段祺瑞陣營。
2.梁啟超歐游后辦學熱情
1920年,梁啟超同張君勱商量歐游回國后自辦大學的計劃,張君勱提出意見:“弟意與其自辦大學,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輸精神,何必負辦學之責任乎”(民國九年一月十二日張嘉森《與溯初吾兄書》)。而此時梁啟超在上海中國公學有演講,以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讓“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說》,民國九年三月十四日《申報》)。結束后,梁啟超不改想法,“欲在上海辦一大學,彼若有志相助最善”(民國九年三月廿五日《與思順書》)。4月3日,中國公學常務董事梁喬山病歿,董事會湯化龍、王敬芳等人一致邀請同為研究系的領袖人物梁啟超接掌中國公學。
梁啟超管理中國公學
梁啟超為中國公學的發展耗費了大量心血,“吾將以此為終身事業,必能大有造于中國”。受到同仁稱贊,“中國公學者,諸友人精神之寄托者也,倘公學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擴而大之,諸友在天之靈,其歡欣感佩可想也”(民國九年五月十四日王敬芳《致任公先生書》)。雖然梁啟超對中國公學的直接管理只有4年(1920-1924年)的時間,但卻解決了很多問題。
1.梁啟超籌集經費
梁啟超寫信給女兒,希望其幫忙勸捐款,“茲有寄林振宗一信,并中國公學紀念印刷品兩冊,可交去并極力鼓其熱心。”指出“彼若捐巨款,自必請彼加入董事會,自無待言,此外當更用種種方法為之表彰名譽,且令將來學生永久念彼也”。并且提到利益實惠,“林君欲獨立辦礦,或與國內有志者合辦,吾皆能為介紹也”(民國九年七月廿日《與嫻兒書》),即學生丁文江從事地質研究,熟人劉厚生投資辦礦。經費一直是中國公學未能解決的問題,后來梁啟超以其稿費墊付,“頃中國公學購地建校舍,尚缺數千元。弟寄售之<中國歷史研究法>計尚有千余元”(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書》。
2.提高中國公學名聲
梁啟超等人積極邀請哲學大家羅素前來中國公學演講,“頃函商聘請人用何名義,弟復書謂用中國公學名最好,或加入新學、尚志兩會亦可”(民國九年七月三十日《致伯祥溯初兩兄書》。并于1920年9月以中國公學為大本營創立“講學社”,“該社名義上仍是私人組織,任公在發起講學社時,決定不完全依賴政府。”講學社的創立有其目的,“籌劃此事過程中,梁啟超、王敬芳等頗有借此為中國公學揚名之意,前揭建議‘以中國公學出面邀羅素’即是例證。此外,梁主張‘講演或先在南舉行最佳’,亦見其抬舉中國公學之心。”羅素來中國的第一場演講即在中國公學,中國公學名聲由此打響。
3.中國公學改辦大學
梁啟超1920年發布《吳淞中國公學改辦大學募捐啟》,明確提出要將中國公學改辦為大學:歐戰以后,文化日新,我國民順應環境之趨勢,國民自覺心之發達,一日千里,乃共憬然于學問。基礎不植,在個人無以自立,在國家無以圖存,莘莘學子,欲求高尚完備之學科,若饑渴之于食飲也。而環顧國中學校狀況,欲求一焉能與各國最高學府程度相頡頏者,竟不可得。即有一二較完善者,則大抵在北方,而南方幾于闕如。又多屬官辦,常為政治勢力所牽制,不能遂其自由發展……本校既有可寶之歷史,有相當之設備,同人等承乏校務,不敢不自勉,決擬于明年為始,改辦大學,學科講座,不求泛備,惟務精純,視力所屆,歲月增廓,圖書儀器,廣為購儲,藉供學生自由研究。
但這一計劃遭到蔣百里反對,“我輩談教育亦須有一種特別精神,就是喚起人的研究心,不是僅僅販賣貨物,授人以學,如其一掛大學招牌,則內容無論如何,精神即為此二字掩住。”同時,其亦反對梁啟超任校長,“任公萬不可當校長……任公惟做講師,才能把他的活潑潑地人格精神一發痛快表現出來。”認為中國公學的擴充“早稻田、慶應都不足法,白鹿洞、詁經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價值”(民國九年蔣方震《與東蓀吾兄書》)。不過張東蓀給予了梁啟超支持:
蓀以為近代學術與古代學術不同,故近代教育與古代Academic(講學舍)不能盡同,故前言之講座辦法,實調和近世大學與古代講學舍而具其微,若夫純采講學舍辦法,在今日必不足號召,則學生來者稀矣……故辦學事,非大家提起興會,以助長任公之興會不可。因此弟不贊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為中心,而以為應以“一團人之人格為中心”,此團不限于吾輩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民國九年十月張東蓀《致任公先生》)
最終于1922年由教育部準許中國公學商科升格為大學,但梁啟超沒有任校長一職。
4.中國公學學潮問題
中國公學1921-1922年發生了“驅張逐舒”學潮,但在梁啟超的調節下都得以解決。1920年張東蓀“對于政治,厭惡已深,以后誓不為政治性質的運動……將來如有教育事業可為者,弟愿追逐于當世諸公之后。”梁啟超以教務長身份將張東蓀招入中國公學,進行學制改革,“課程內容逐漸改革,中學實行三三制,商科亦分銀行、會計、秘書、貿易各門講授,以期實用。”并得到稱贊“他辦學時候,據我所知道有兩大特色:一是毫無黨派成見,專門聘請好的教授;一是積極充實圖書設備,提倡自由研究的學風。這話是在那時中公畢業及讀過書的校友都能負責證明的。”
1921年張東蓀助舒新城進行“新教育”改革,遭到舊制師生反對,引發學潮。梁啟超指出,“最多再鬧風潮一兩次,愈鬧一次則阻力愈減一分,在吾輩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約諸賢,無論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處別謀進展,其難亦正相等,天下豈有無風波之地耶?”(《民國十年《與百里、東蓀、新城諸公書》)其后舒新城致書信給梁啟超,“公學事大體已解決……不再言辭職也……現擬將中學部組織變更,大致仿南開辦法,暫分設教務、訓育兩股,每股由專任教員一人負責,如此對學生處理事務之法人多。”并認為新招教員,“為吾黨用,弄風潮亦大有好處也。”(民國十年十一月廿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
“黨化教育”與中國公學
梁啟超以政治過渡文化,而最終以文化回轉于政治,是社會進化必然的雙向妥協,也是歷史局勢所決定的,但派系斗爭下的不穩定性決定了中國公學面臨“被占有”的危機。
1.“研究系”學權爭奪
中國公學最終是以學權掌控作為研究系“派別勢力”的,“中國公學委城與南陔、東蓀三人辦理,君勱、志摩則分在南開講演,公則往南京講演,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后吾黨將遍中國。”(民國十年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在公學保息問題上,更將其上升到研究系事業的存亡,“蓋公學生命即在六萬一事……彼時吾輩在南方,左有自治學院,右有中公大學部,自可與北大、東南鼎足而立……望先生以全力進行,非僅公學生死關系,實吾輩事業生死關系也。”(民國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希望以教育和實業影響政治,“將來的社會中心勢力,非托與學者與商人之團體不可……黨債保息事,不但為公學生死之關頭,而亦我輩對于國家前途所懷抱之成敗。”(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陳筑山《致任公先生書》)
2.中國公學“改朝換代”
1927年,北伐軍占領上海,張東蓀被“目為學閥,加以通緝”,中國公學由國民黨掌控,研究系“統治”結束。私立中國公學的沉浮是近代中國教育的縮影,但時代背后不可逆轉的新思潮仍促進了中國公學地發展,也有著梁啟超等人的功勞。
參考文獻:
[1]章玉政.《光榮與夢想:中國公學往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
[2]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3版.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33:250.
[3]丁文江,趙豐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415-537.
[4]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1版.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193.
[5]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第1版.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72.
[6]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64.
[7]張東蓀.《張東蓀致張君勱函》.解放與改造,1920:18.
[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部. 近代史資料.總第131號[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145.
[9]俞頌華.《俞頌華文集》.第1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