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摘 要:今天的西部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學上的名稱,這個神秘而充滿傳奇的地域已在社會意識形態及經濟發展下有了新的表征。雕塑語言作為城市視覺、觸覺觀能認知的重要范式,是地域文化建設的主要手段。矗立于西部這樣一個特殊地理學、文化學、社會學多元角度上的空間雕塑,應與其恒定的西部文化形態相呼應。在中華民族內向、深沉的審美視野中,西部是一個悲愴卻強悍不屈的生命體,處于亞歐大陸制高點的西部那漫天的風沙、廣袤的大漠山川體現了中國別樣的荒原美學。文章從已落地的西部雕塑案例出發,論述了荒原美學在西部城市雕塑中的詩意表達。
關鍵詞:荒原美學;西部;雕塑;詩意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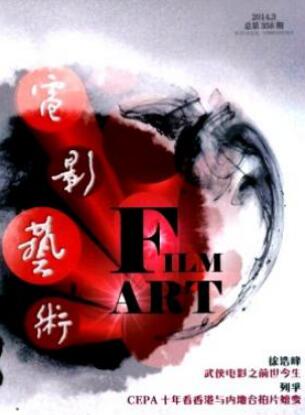
今天的西部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學上的名稱,它已成為具有多種語境的文化象征,這個神秘而充滿傳奇的地域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意識日新月異的后工業時代已有了新的表征。中國西部有遼闊的草原,有奇異的山嶺,有無垠的大漠,有險峻的峽谷,有奇異的丹霞地貌等。蒼茫與壯美、質樸與神秘,構成了西部富有魅力的精神本相。今天的西部是無數目光與話語匯聚的場地,不僅因為這里曾是絲綢古道,更因為這里繁衍生息著多民族的中華兒女。多民族交流與共生,人與自然相立相融,歷史的興盛衰亡、命運的流散際會、自然的枯落榮生在這里演繹著西部獨有的畫卷。
在中華民族內向、深沉的審美視野中,西部是一個悲愴卻強悍不屈的生命體。處于亞歐大陸制高點的西部那漫天的風沙、廣袤的大漠山川是中國別樣的荒原美學。“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夕陽西下”“西風送冷”,西部成為中國荒原美學中最重要的自然意象。西部人與自然、社會及自身存在的沖突和超越是人生價值的深層體驗。“快倚西風作三弄,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 這是天、地、人三者和解下的西部生命共感之美。這一特殊的西部荒原語境,建構了西部雕塑語言基因的荒原審美和悲憫關懷的特質。這一特質是對文化與生命價值的深度思索,這是跨越時空的美學精神。
一、《大唐西域記》的詩意傳達
在西部深沉的審美視野中玄奘西行便是荒原美學下的重要精神典范。公元7世紀,玄奘從西安出發,途經廣袤的高原、險峻的峽谷、荒蕪的戈壁、險峻的山嶺,走過那皚皚雪域,穿越荒無人煙的大漠,九死一生,經過五萬多里的行程,歷時17年,憑著堅定的信念,抵達佛教的圣地,研讀佛學,遠播中華文明。玄奘是西部悲愴卻強悍不屈的生命體典型代表,已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圖騰。雕塑家陳云崗的《大唐西域記》,這一雕塑作品把作為中國民族精神典范的玄奘的精神力場以一種獨有的中國寫意風格和東方美學選擇把人物融于自然之中,以中國人文特質的美學思想和精神信仰在雕塑語言中賦予《大唐西域記》以新的審美內蘊,把地老天荒的山水長卷切入到雕塑語言中,衣帶如川,氣勢如虹,山水雕形,刀痕塑神。陳云崗先生以一種比較長的、一種舒展的構圖方式,將大漠山川、雪域高原、沼澤草地、山寺廟宇與人物的形象融為一體的方式來塑造《大唐西域記》,將玄奘求法的過程當中所經歷過的風風雨雨、山山水水與生命和精神的本原融為一體,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荒原美學的精神價值。陳云崗先生雕塑語言中宏厚質樸的生命力量、寫意抒情的詩意表達,將荒原的美、生命的質、精神的核構筑成城市文化的典范。我們這一代人生活在物質極其富裕的當下,苦難經歷的匱乏會弱化我們對祖國此時此刻偉大輝煌的感觸。如今歷史斷裂,現實精神沖突與缺失,正需要城市雕塑這樣的語言形態拉近歷史與我們的距離,在雕塑語言無窮無盡的微妙張力中建立我們的精神家園,并內化成一個民族的生存信念。《大唐西域記》在對東方母語的眷戀中和中國精神的堅持中,實現了人對有限生命的超越,同時實現了雕塑語言的詩意傳達。
二、《絲路傳奇》的精神表述
西部這片缺少生命之水的荒蠻之地,干旱、風沙、寒冷肆虐。艱苦的自然條件一直伴隨著這片土地上的生命體,在人與自然、自然與人相伴相輔的成長中始終不可缺失的是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體與自然的抗爭,這使得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也必然孕育著更寬廣的生命意識的發展軌跡。在人類對自己生命的意識和對大自然認識的探索中,神話故事從來都是人類反思自然與自我的反映。《絲路傳奇之三——甘州麋潞》講述了發生在絲綢之路中段甘肅張掖的一段人與動物共同與自然抗爭且宣傳慈悲報恩神話故事。鹿以其角之神異之力,對生者于陽界及死者于冥界的生活起到保護作用。在絲綢之路中段的甘肅張掖有著中國的少數民族裕固族,這個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在這個民族里口口相傳著許多關于人與鹿共同抗爭自然的故事,同時這個少數民族的聚集地也是中國鹿養植的重要基地。鹿的全身都是寶,鹿茸、鹿胎、鹿心、鹿血、鹿筋、鹿鞭、鹿尾等都是珍貴的中藥材。鹿自古野生有之,自商周圈養鹿起,就有鹿骨占卜、鹿角刻辭、鹿身入藥,在人與自然抗爭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裕固族這樣一個以鹿為重要生活與情神給養的民族中,鹿成為西部人民向往美好、企盼幸福的重要寄托。《絲路傳奇之三——甘州麋潞》以雕塑語言再現了絲綢之路上的神話故事,化景物為情思,以流動的韻律表現了載著幸福的美麗少女舉目眺望憧憬著西部美好的未來,神鹿與少女都是表達西部精神與美的意象符號。西部本體神話故事的價值不僅是文化的傳播,還具有豐富深厚的藝術意蘊和生態觀念,也是生命深處洶涌蓬勃的力量,是西部人民生命意識的熱望升華。
三、《蘇武牧羊》的荒原語境
在這片荒原美學視野下,“扶伏民”家族的身影不僅是中國歷史及文化不可或缺的存在,亦是荒原美學的形象傳達者。《古小說鉤沈》輯《玄中記》:“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后是為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在中國漫漫的歷史征途中,在西部漫天黃沙的荒漠里,“扶伏民”是政治流亡者、精神流亡者、生活流亡者的歷史濃縮。在西部漫漫的黃沙中,人與自然的抗爭、政治與歷史交融下的悲壯記憶比比皆是。“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無貴無賤,同為枯骨……”,這是西部荒原美學下的千古絕唱。
蘇武便是這千古絕唱中的重要聲部。蘇武出使西域被扣留十九年。“天雨雪,臥嚙雪,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蘇武持節不屈、歷盡艱辛終得歸鄉。蘇武孤獨卻堅定、頑強的腳步踏著西部這片荒原的記憶,他不屈的精神生生不息地在這片土地上傳承。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人民政府在政府府志的冊頁上發現了蘇武在甘州的黃土地上牧羊,隨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挖掘這一西部美學及精神領域的典范——蘇武,讓他的身影矗立在了長長的絲綢古道上,讓西部特有的荒原美學及蘇武精神留存、傳播、交流、再生。
年邁的蘇武在羊群中孤寂地注視著東方,悲愴卻又堅毅。群羊托襯著他的孤單,寫意的雕琢手法表現了群羊無力、哀苦的眼神與蘇武炯炯有神的堅毅目光,兩者形成強烈的對比。蘇武的整體人物刻畫上突出了面部的塑造,衣紋虛化處理,隨勢起伏,在線、面、塊的刀與石的碰撞中表達著生命的頑強。不屈的精神、堅定的目光與人形成一場心靈的對話,在寂靜中讓中華精神永恒傳承。蘇武沉默著,卻是此處無聲勝有聲。歷史被凝固在這一瞬間,突破時間的界限,訴說著曾經的風霜,這無邊的寂寞、偉大的沉默感動我們的同時也讓我們思考著人生,給我們心靈帶來深深的震撼。看得見的歷史是城市和文化的對接,可碰觸的記憶是人與精神的共鳴。
今天中國雕塑正以前所未有的氣度向世界昭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與西部大開發的浪潮中,雕塑這一富有活力的學術領地一定會為西部大開發增光添彩。向優秀的歷史經典致敬,尋新的審美理想,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當代雕塑的原創力與蘊含的人性與理想之美。在這樣一個視覺文化盛行的時代里,愿我們以謙卑的姿態面對文化,面對歷史,面對未來,把西部乃至中國凝固的文化與精神流傳千古、遠播四方。
參考文獻:
[1]丁方.凝固的美[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焦興濤.新具象雕塑[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3]趙萌.中國雕塑藝術[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
[4]黃向陽.全球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J].社會科學家,2007(1).
[5]閻文儒.中國雕塑藝術綱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作者單位:西安美術學院公共藝術系
推薦閱讀:動畫科技論文當代美學下的動畫藝術